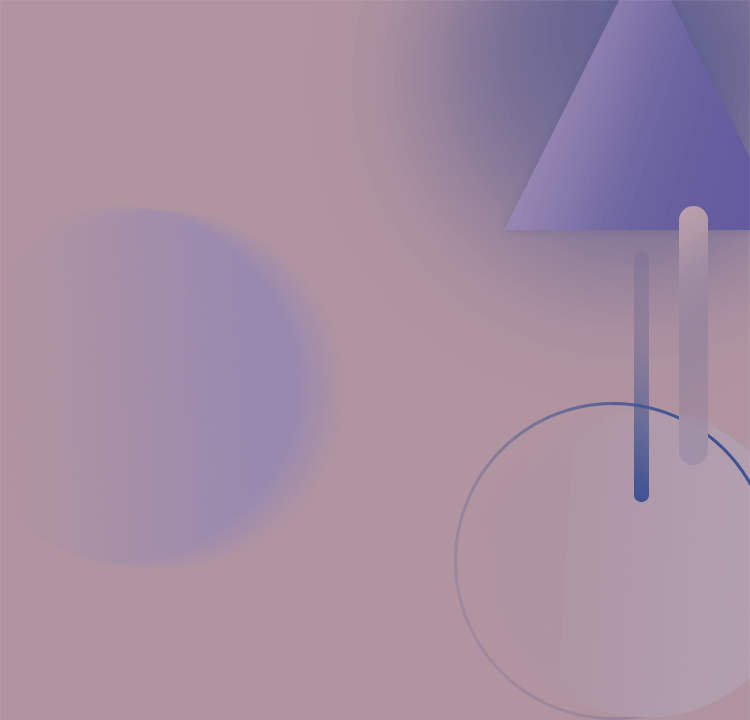尼泊尔游记(五)一沙一尘埃 一花一世界
2019-4-26一 烧尸庙
这世界很大,真的有人在你未知的地方,过着你完全未知的生活。
尼泊尔的烧尸庙就是一种文化冲击。如果去尼泊尔没去过烧尸庙,看过火葬,真就别说你去过那儿。
烧尸庙本名叫“帕斯帕提娜”神庙,是尼泊尔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神庙,也是南亚地区供奉湿婆神的四大神庙之一,湿婆神是尼泊尔人最崇敬的神灵,具有毁灭和创造的力量。
尼泊尔的印度教徒不仅把帕斯帕提娜庙视为神殿,也把流经帕斯帕提娜庙下的巴格马蒂河视为圣河。
巴格玛蒂河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最后流入印度教徒的天堂-恒河。
印度教徒们平时经常在河岸祈祷,在河中圣浴。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躺在帕斯帕提娜庙下面,把双脚伸向河里,任圣水将它洗净。而死后能在这里火化,自然就成了他们灵魂奔向天堂的最理想的地方,他们坚信,在湿婆神的庇护下,骨灰最终流向恒河,灵魂就会脱离躯体,得以解脱,得以重生。
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有约32亿的基督教徒,11亿的伊斯兰教徒,2亿的佛教徒和10亿的印度教徒。
10亿印度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尼泊尔有86.2%的人都是印度教徒。按印度教的说法:“一个灵魂有8400万次生命,每进行一次轮回,就会提升一个层次,因此,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
只是,1600多年来,印度教徒以骨灰的形式,每日里不间断地流向恒河, 而同时,还有人在恒河里游水、洗浴…… 这要有多么虔诚的精神!非印度教徒难以理解和接受。
本来行程的第一天晚上就安排参观“烧尸庙”,伙伴们一商量,恐怕看完了这么让人发怵的场面影响下面的游程,遂和导游商量,安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个行程。
1月24日清晨,早早起来收拾行装,天空阴沉沉地,时而下着稀稀落落的小雨,这到符合今天的意境。
下了车,戴上口罩和帽子,全副武装,只露出眼睛,紧跟阿龙前行。
帕斯帕提娜神庙只接纳印度教徒,阿龙把我们带到她的对面,中间隔着巴格马蒂河,河中有一座人行桥。
此时,对面的六座平台静悄悄的,台子上已经有架好的树枝,但还没有开始烧尸。 我们脚下,竖立着一排排风格统一、规模一致的小型敞门塔庙,庙高5-6米,长宽约2米左右,约有五六十座。这种四面有着圆拱形庙门的塔庙里,里面供奉着象征湿婆的林迦(男性生殖器),或者湿婆神的坐骑公牛南迪。
阿龙指指点点地告诉我们:六座台子中,人行桥以北(就是我们的正对面)那两座是供皇室和贵族专用的,位于下游的四座平台则是贫民百姓的烧尸台。别小瞧那两座台子,1955年特里布文国王在瑞士去世后,遗体运回国内,在这里焚烧的。2001年震惊世界的“王宫惨案”发生后死亡的10位王室成员,也是在这里火葬的,当时台子不够,临时搭了好几座。
阿龙又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的叔叔曾经是尼泊尔的水利部长,2015年去世,也是在这里火葬的。
听着阿龙介绍着印度教的风俗,望着眼前承载着印度教徒无限期望的巴格马蒂河水,心中不禁感叹,无论死者身份多么高贵,对待死亡,通往往生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漂浮在河水中的骨灰没有贵贱之分,只有一个方向--恒河。
说话间,大约9点钟,陆陆续续盖着黄色披盖的死者被抬到这里,阿龙收住了话语,我们瞪大眼睛,静静地看着对岸的火烧仪式。
只见其中一个抬着死者尸体的担架先是放到了烧尸台旁边的台阶上面,烧尸台的木柈上铺上了黄色的流苏样条绒,支起的四根木杆上搭了一个小小的黄色罩盖。死者的家属拿着一个碗,在巴格马蒂河上盛上了一些水,然后滴入亡者口中(阿龙悄声说,这是为了验证是否死亡,若是咽下了这口水,说明人还活着,其实,一般情况下死者都在家里放七天,不可能有生命,这只是个形式)。
证明了亡者已经没有生命,众人小心翼翼抬起担架,走向位于上首的烧尸台(这人一定是贵族或者官员了),在台上环绕三圈,再把尸体头朝帕斯帕提娜神庙,足向巴格马蒂圣河,放在木架上。众人肃立在火化台的边上,为死者祈祷,有人在轻声哭泣。一个身穿白色衣服(丧服)的家属走上来,按顺时针方向围着死者绕行三周,同时不断向死者身上撒放花瓣。接着,有人抱来了干柴,覆盖尸身,有人拿来火把,从死者的颈部开始点燃,只见滚滚烟起,渐渐地熠熠火明,人们不断地用一根长杆翻搅着尸、柴。冲天的火焰把骨灰吹上了天空,火借风力,空气中仿佛有焦灼和呛人的味道,同行伙伴有受不住的,落荒而去。
当持杆人确认尸和柴烧得差不多的时候,便用力将闪着余火的骨灰和未燃尽的木炭推入河里,随着烟汽腾起,一个曾经活跃的生命,就此灰飞烟灭。


观看整个过程的我,松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从当初的恐惧,到此时的忘我,仿佛进入了一种从来没有的境界。
我竟然体会到亡者离开世间的踏实感。也许,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她)心中最大的依赖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在湿婆神的注视下,在湿婆神身上最强大的“林迦”庇护下,安全感已然包围了他的灵魂,死,不再是让人痛苦的事,他像一个游子,在母亲的怀里安然入睡,在母亲的怀里走向梦中的世界……
若是把生死看透,一切都淡然。他们没有留给后人可供瞻仰和祭祀的墓穴,即便是名人也没留下墓志铭,对于他们来讲,死亡是超脱,是踏上轮回之路的又一次旅程。挥挥手,我轻轻地走,就如我轻轻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
来自尘土的终归还是要归于尘土,恒河的水带走的是物质元素,是对往生美好的向往。世间的人们仿佛是无际沙漠中的一个沙粒,一个在空气里看不见的尘埃,渺小而倔强地存在,一沙一尘埃,宿命在路途中。
二 苦行僧
此刻,苦行僧拉迪巴巴和沙德利巴巴就在我身边,在我观看火葬的地方。

在尼泊尔的旅途中,经常会看到苦行僧的身影,他们被看成是来凡尘普度众生的“神的使者”,苦行僧被尊称为“萨杜”或者“巴巴”。
印度教认为,人需要经过多次轮回才能进入天堂,得到神的关照。而有些人希望走捷径,在此生就得到神谕和真经,苦行僧就被认为是这样的一条捷径。苦行僧的主要任务就是冥想修行,通过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为简单的程度来追求心灵的解脱,摆脱无尽的轮回之苦。
苦行僧们采取斋戒、日晒、禁食、沉默等各种形式进行自我苦修、磨砺,期待忍受自然环境的压迫得到某种超自然的神力。
苦行僧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在烈日下、深山里、福舍中打坐;或在庙里为教徒额头涂红点,送去祝福;或者手拄象征湿婆神、毗湿奴的三叉杖,边走边吟经文。苦行僧们必须做到“三不”:不性交、不撒谎、不杀生。
苦行僧的“苦”非常人能忍受,达到的境界也非常人能做到。曾经有人在尼泊尔遇到两个年长的苦修者,一个练瑜伽,轻而易举把双脚盘到了脑后,而另一个,不知道自己有多大,修行了多少年,当他把头上从未洗过的长发解开时,足足有3米长,臭烘烘地铺洒了一地,里面寄生着各种小虫小蚁。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何以忍受噬咬、叮痒。
据说印度有个最牛的苦行僧,叫阿尔马克杰,高举右臂46年,至今没放下,如今已经被人们供奉为湿婆守护神。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还有一种苦行僧,居住在福舍(为往来的修行者、旅行者提供的可以遮阴避雨的庇护所)里,一边修行,一边满足游客的要求,拍照留影,但是,要收费的。
拉迪和沙德利巴巴属于最后一种。
我们到的时候,他们还没起床,阿龙把大家凑的小费交给了他们,看到可爱的money,他们开心地出来了。


今年70岁的沙德利巴巴有些内向,也许是年龄的缘故,他跟在拉迪的侧面,感觉是陪同。而51岁的拉迪有些大大咧咧,素面、半裸地从福舍里出来,手里拿着湿婆出场的家什:木杖、眼镜蛇(布做的)、万寿菊花环、女神图片。还有镜子、染料盒。
尾随着他们来到一处有阳光的地方。已经化完妆的沙德利巴巴围上一个毛毯坐了下来,任由大家合影。而拉迪开始编织他那长长的头发,在左上方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又对着镜子涂抹面孔,最后,开始往身上涂白色的灰,完毕后冲我们一笑。
我悄声地让阿龙问他们,每天是否冲浴?还有,身上涂的灰色粉末是什么?
之前听说有的苦行僧身上涂的是骨灰,若是这样,真是让人望而生畏。
拉迪爽快地告诉阿龙,他们每天早上都冲澡,他身上涂的是香灰。
哦,我悄然地松了一口气,凑近拉迪,开始搭话。我问他,头发攒了多少年?他用英语回道:17年了。
伙伴们开始和拉迪照相,拉迪也很配合地摆着各种pose。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尼泊尔一月份的天气阴凉,我们都穿着棉衣,而拉迪一直裸着上半身,我发现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跟他说:“拉迪巴巴,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别冻着,这样会感冒的。”拉迪似乎被感动了,拍拍他身边的坐垫让我过去,给我额头上涂了一个祝福的红点,又把象征吉祥的万寿菊套在我的颈部,口中念念有词:Long live and happy (幸福长寿)。我双手合十向他致意。
我一句不经意的话得到拉迪如此垂青和祝福,看来修行的人也是有情感的。

告别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又拿出五张一块钱人民币,两张放在沙德利面前,三张给了拉迪,然后双手合十微微鞠躬,向他们致以陌生人的祝福,而他们也一直双手合十向我表示感激之情。
有人说,这样的苦行僧有表演的成分,不屑一顾。于我来讲,即便是表演,也值得尊重。
舞台上的演员是一种职业,传递着文化。而拉迪和沙德利是生活中的演员,给了我们接近印度教、了解印度教和苦行僧的机会,只为在寒风中裸着身体工作就是一种敬业,报酬是应得的回报。
在印度教的神话里,梵天是世界的造物主,他诞生于一朵莲花。莲花在佛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莲花代表着神圣、纯洁、高雅和复活。
在我眼中,每一个修行的人都像一朵莲花,苦行僧、活女神、印度教徒、佛教徒……心中有仁爱,莲花必自开。
“一花一世界”,种花的人修的是自身的宇宙,求的是至善、至真、至美。
愿这世界处处开满莲花,愿这世界充满了祥和、安宁。
也许是苦行僧带来了湿婆神的幸运庇护,回返的飞机上,不负我的期望和等待,清晰地看到了心中的圣山“珠穆朗玛峰”,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两年前,我曾在珠峰大本营看到她的侧影,那时已觉幸福满满,没想到有一天,我从她伟岸的上峰掠过,直视她的丰姿。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让你忘掉时间的存在,而在尼泊尔的每一天、每一刻都让人陶醉,我觉得时间抛弃了我,把我的魂丢到了尼泊尔那片神秘的土地,至今!
备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和队友,一并致意。
作者:于秋月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
《散文选刊.下半月》签约作家
展开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