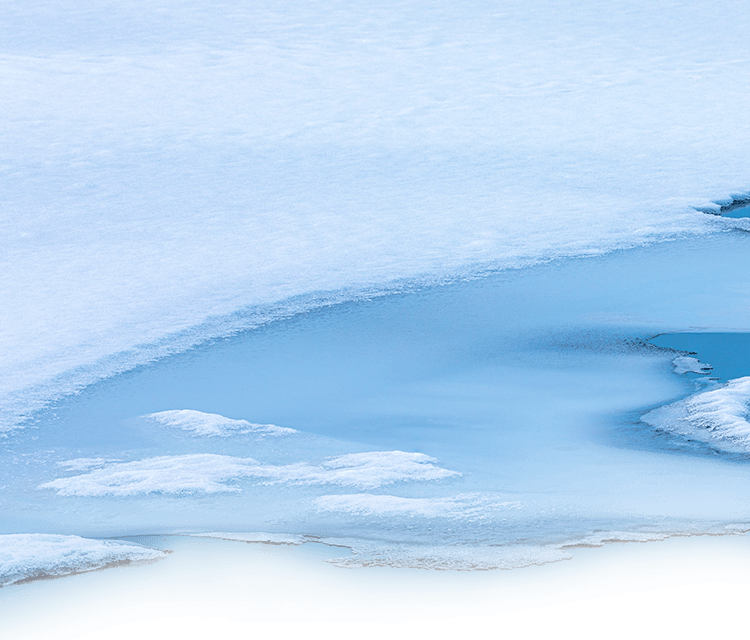凌 波 仙 子
2026-2-7清水白石间,案头的水仙亭亭而立。瓷盆里的清水映着疏朗的根须,白如凝脂的球茎沁出细润的水光,细长的绿叶托起那轻盈的花朵。六片洁白的花瓣舒展如蝶翼,中央那抹鹅黄的副冠,恰似缀着碎金的流苏。凑近细嗅,一缕清芬便漫入鼻腔,不似梅香清冽,不似兰香幽远,而是一种清新脱俗的味道,丝丝缕缕缠绕鼻尖,涤尽冬日的沉郁。 一盏清水,一束鲜花,一缕清香,一颗至诚清净之心…


水仙临寒吐芳,清芬远溢,为花中雅客;它的根似蒜,叶如兰草,绽放时碧波映花,宛若仙子凌波而立,故而称凌波仙子;因它不可缺水,又称水仙。 常见水仙主要分为两类:单瓣者,花瓣洁白、副冠金黄,形如盏台,故称“金盏银台”;重瓣者,花瓣层叠、玲珑如玉,故名“玉玲珑”。二者并置,暗合“金玉满堂”之吉祥寓意,历来象征富贵与祥瑞。




想来这水仙,原是从古诗词里走出来的精灵。宋·黃庭坚:“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宋·杨万里:“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宋·刘克庄:“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妍”;明·梁辰鱼:“幽花开处月微茫,秋水凝神黯淡妆。绕砌露浓空见影,隔帘风细但闻香。”;明·李东阳:“淡墨轻和雨露香,水中仙子素衣裳。”,古人的笔墨早已将它的神韵描摹殆尽。而此刻案头的这株,正以无声的绽放,续写着千年的诗意。它不与桃李争春,不与菊桂斗艳,只在寒冬里默默吐芳,用一抹青绿、一缕幽香,唤醒人心底最柔软的诗意,让漫长的冬日也有了温柔的盼头。




水仙是草本花卉中少有的可雕刻的珍品,水仙花雕刻艺术延续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水仙雕刻,一门艺术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让水仙花焕发新生。雕刻过程包括净化、开盖、疏隙、剥苞、削叶、刮梗等步骤,经巧手雕刻、水养,可塑造成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的水仙花盆景。集奇、特、巧、妙、雅于一身,堪称百花园中的奇葩,不仅展示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也体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与精神熏陶




水仙花的雕刻造型多样,常见类型包括模仿自然形态的创意设计、传统对称风格及立体层次雕刻等,具体可分为花篮(蟹爪)、凤凰回头、传统圆形、扇形展开及多层次立体五种。





水仙迎春,这腊月里的小小仪式,已成了人们刻在心底的美好,平凡的日子,因这份期盼与芬芳,多了几分诗意。那缕淡淡的香,也是游子归乡的讯号,是全家团圆的伏笔,是岁月铺展的温柔底色,让奔波的脚步慢下来,让漂泊的心有了归途。 新年的美好,从一盆水仙开始,缓缓铺展,水仙开处,便是人间好时节。

展开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