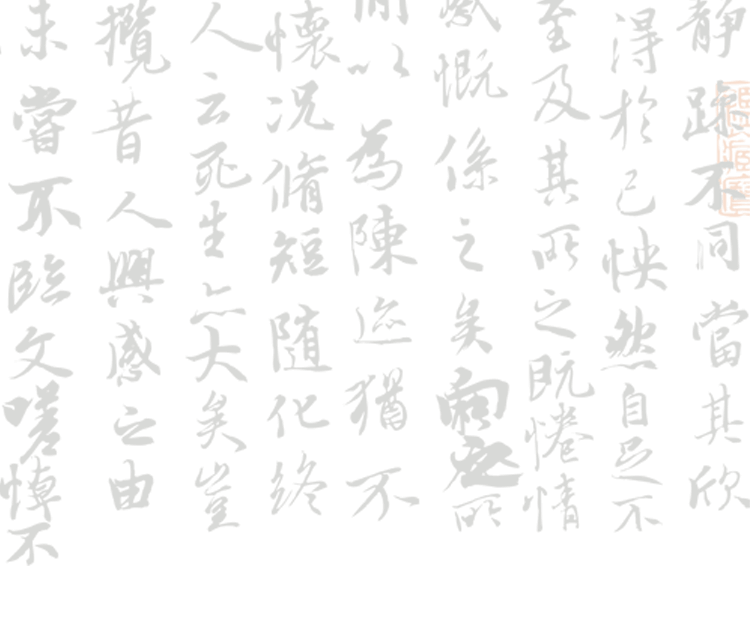第26讲:填词的章法艺术
2017-11-10章法,指词体的篇章结构及其方法,主要包括起结、过片、开合、转折等内容。章,本指音乐单位,音乐的一曲为一章,后引早为指配合乐曲歌唱的歌词的一篇为一章,诗文的一篇为一章。词,配乐歌唱,和诗的“体形”很不一样,章法当然也有别。词谱虽短小,但词人就是要在这方寸之地争奇斗艳,起转承合,极力使笔下的词跌宕起伏,美不胜收,整体上又要浑然一体。其中,起结和过片,是搭起词这个金屋子最重要的地基、斗拱和梁架。
起 写文章,跟美女打扮一样,最要紧的是头脸,要让人初一见,惊为天人。清代词评家沈祥龙说:“诗重发端,惟词亦然,长调尤重。有单起之调,贵突兀笼罩,如东坡大江东去是。有对起之调,贵从容豆类整炼,如少游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论词随笔)这是从形式上来说起句方法,从内容上来看,词的起法很多,而且要求达到的艺术不能一览无余,要留有神秘感,让他好奇不已,才会引人入胜。宋词常见的开头方式有:
1、以景起 这种方式最为常见,翻开全宋词,信手拈来。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 ——晏殊“踏莎行”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周邦彦“兰陵王” 落日熔金,暮云合壁。 ——李清照的“永遇乐”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 ——吴文英“八声甘州”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辛弃疾“苏幕遮” 凋零寂寞的深秋,烘托了守边将士的无边愁思。辛弃疾一生壮志难酬,这份豪杰的激愤喷射到秋景上,是“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水龙吟的壮阔沉郁。)

2、以情起 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词情笼罩全篇。例如: a、大将军岳飞一开口就怒吼:“怒发冲冠凭栏处”(满江红),真是响遏行云,振聋发聩。 b、李煜在汴京对景难遣心中悲哀,就直直地长叹:“往事只堪哀”(浪淘沙),蓦然而来,真是悲戚彻骨。 词如果用情语开启,情感大多强烈真率,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引起情感共鸣。

3、以事起 先叙事,再就事生发,这种方式远远少于景起句。例如: “无言独上西楼”(李煜“相见欢”); “水调数声持酒听”(张先“天仙子”); “醉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破阵子)。 初看似乎平淡无奇,实际上却引弓待发,紧接着会开出另一番天地景致,或笔锋一转,如悬崖飞瀑,一泻而下,使文势跌宕起伏。

4、以问起 先劈头盖脸地提出一个问题,读者不由得一惊,再回答。“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这种问起法,于千回百转之中喷薄而出,其情感更震撼人心,比直陈更觉摇曳灵动。 当然,也有久叩柴扉久不开的时候,正待要转身离开,却突然发现“一枝红杏出墙来”,这种起法,被形象地称之为“扫处即生”,比如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更出人意料地转出了“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的浪漫来。又如欧阳修《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扫出了花落后喧嚣归于平淡的另一种美。 其实,不管是平起还是刻意突兀而起,词的起法之美在于拉开一道帷幕,戏刚一开声,就赢得了一个碰头彩,更多的好戏还在后头。

结 结与起句一样,词的结尾也非常要紧,往往是全篇的点睛之笔。结句要像勒住一匹狂奔的骏马一样,收束有力,又能发人深思,留有余味,所以词人们在结句上也特别下功夫,或以景结,或以情结,或以问结。 1、以景结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断肠院落,一帘风絮”“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以景结情,悠然而逝,含蓄蕴藉,最能展现词的婉约美气质。也有气魄雄大的词人,以崇高悲壮之景结束全篇,如李白《秦楼月》:“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气象雄浑,冠绝古今。吴文英的怀古词《八声甘州》结句:“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大气包举,壮阔苍茫。前人最推重“以景结情”的方式,如沈义父《乐府指迷》就很有代表性地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

2、以情结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情语结句,多以真率激切取胜,切忌情感表达的轻浮直露。“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如此赤裸裸的呼叫,哪里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许多老夫子深受刺激,当然嗤之以鼻。但现在看来,周大词人原来痴情得如此坦率可爱! 3、以问结 “彬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问得柔情婉转,格外曲折动人。“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末一问,摧刚为柔,令无数英雄堕泪。 以上就内容分类,如按结构技法而言,沈祥龙对词的结句创作作了十分精当的总结:“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结有数法,或拍合,或宕开,或醒明本旨,或转出别意,或就眼前指点,或于题外借形,不外白石《诗说》所云辞意俱尽,辞尽意不尽,意尽辞不尽三者而已。”

表达方法 1、拍合 即开合、呼应、比如柳永《八声甘州》的结句“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与首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遥遥呼应,可知末句以前所写都是词人倚栏杆时的所见所想,前面的抒写就有了着落。 2、宕开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词困锁在深深庭院里,又逢上斜风细雨,天气这样恼人,词人终日为离情所苦。结尾却出乎意烊地宕开一笔,问:“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显出一番欢愉之意,似乎苦尽甘来,曲折婉转,余味无穷。

3、点醒 点醒是指点明词旨,往往是“辞意俱尽”。如刘克庄的《玉楼春》(戏林推)“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如果单看前六句,似乎只是戏谑林推长年在外冶游狎妓,以为是游戏笔墨。词到结尾,突然推出“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两句,劝勉热血男儿去西北收复神州失地,干 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卒章显志,使人猛醒回头! 4、翻出 结句与前面的文字截然不同,是一种巨大的落差或逆转的关系,这样能把情感表达得更加深透有力。如辛弃疾的壮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前面一路大刀阔斧,快如霹雳,正当读者为激烈的战斗感到酣畅淋淳之际,结句却陡然翻出一声悲叹:“可怜白发生!”猛地跌入悲惨的现实,好似一桶冰水泼烈火上。前面九句和最后一句形成巨大的反差,大起大落,读者不禁为词人扼腕痛息!如果只是一味的哀叹,哪有这般翻出之妙呢?

好的结句,从美学风格来划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即清人沈谦所说: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 ——《填词杂说》 词的起结之法很多,如果更概括地说,可用刘熙载的说法:“起句非渐引即顿入,其妙在笔未到气已吞。收句非绕回即宕开,其妙在言虽止而意无尽。”

过片、换头词调多为上下两片,跟小说、电影分为上下两册/集一样,表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两个层次虽然形式上分开,内容必定要密切关联。这个上下片之间的桥梁作用,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下片开头,即“过片/换头”的身上。过片,是词特有的章法,词人、词评人都十分重视,他们强调“过片不可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张炎《词源》)承上接下是总要求,一般来说,上下片分别吟咏情景、今昔、内外、来去、昼夜、虚实等不同内容,但上下两片要接得紧密、自然,又以能出新意为上。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若才高者方能发起新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周济《介存斋论词》说换头:“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皆须令读者耳目振动,方成佳制。”这都是前辈对过片做法的精彩描述。

过片以“笔断意不断”,或者说是“藕断丝连”为最妙,姜夔《齐天乐》的过片“西窗又吹暗雨”常被做为典范。整首词细致摹写了蟋蟀私语般的悲鸣声、机杼声、暗雨声、砧杵声、丝竹声等 各种声音,将虫声与愁情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很难截然分开。作者却奇妙地抓住了“西窗又吹暗雨”一句作为过片,上片歇拍已经说到“夜凉独自甚情绪”,谁知西窗外又隐约传来冷雨敲窗声!一个又字既把上下片的情景紧紧地连接起来,又使之明显地划成两段,岭断云连,手段确实高妙!

过片的具体做法多种多样,并无定规,常用的以下几种: 1、上下紧相连,换头笔断意不断。 这是最普遍的作法,如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作者先写俯瞰郁孤台下饱含着无数难民血泪的江水,然后写举头北望故都,丛山苍莽遮断了目光,上片歇拍“可怜无数山”,以山字结束。下片接着从山说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青山又回应到江水。两山相连,衔接紧凑。换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2、上下不相连,换头另起一端。 看上去,好像上下片说的是两件事,仔细一看,才发现整个的意境、感情、气脉是完整贯通的。如苏轼《卜算子》,上片写幽绝的夜境,下片单咏孤鸿。好像上下片截然分开了,但上片歇拍“缥缈孤鸿影”将上下两片连接起来了,上片写幽人,幽人孤独如孤鸿,下片写孤鸿,孤鸿幽恨如幽人。全词语语双关,词人托物寄寓了自己初贬黄州期间的苦闷和孤高的复杂情怀。还有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也常被人议论,说它上片写昼景,下片专咏石榴。上下片并非前言不搭后语,都紧紧扣住了榴花与美人的孤芳高洁、自伤迟暮的品格和特征,花人合二为一。虽是别具一格,却别饶韵致。像这种上下片不相连的,换头总是异军突起,完全换了另一幅头脸,但意脉还是暗中相连。

3、上下相对比,换头是过桥。 或一正一反,或一今一昔,或一问一答,而以过片为桥,上片首紧承上片尾,使上下片贯通一气。如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上片追念昔日帝王生活,下片哀诉今日亡国之君的凄凉,一今一昔,一正一反,对比十分鲜明。过片处,上片以“几曾识干戈”作结,下片以突然间作了敌人干戈下的囚虏起首,互相照应。陈与义的《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情况近似,上片追忆南渡前在洛阳时的豪酣岁月,下片抒发如今偏居江南一隅的惆怅之情,过片“二十余年成一梦”,承上启下。

广为人知的一首小令,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明白如话,一说是朱淑真的独白。词的上下片也是今与昔的鲜明对比:“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花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上下片结构相同,换头只是换了一个字,就将昔与今、闹与静、欢与悲、笑与泪处处比照着,充分展示了物是人非之感、旧情不再之痛。 吕本中的《采桑子》除叠句用得巧之外,有意思的是,它的上下片格式也一致,内容却完全相反。词以“明月为喻体”,上片“不似”下片“似”,一正一反互为矛盾,却和谐地统一为一体,真是妙趣横生,其中的奥妙在于两片开竭泽而渔那个恨字,一要感情的红线将上下片看来对立的意象连接在一起,正说反说,反正都是因为爱。

还有用问答来结构词体的。如敦煌曲子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多满语),上片是思妇问灵鹊,下片是灵鹊的答辩,一问一答,全由对话组成,是很有创意的写 法。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也有问答结篇之妙,上片以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作结,整整一个下片都是答语,以“我报”领起。 像这类上下片对比比较鲜明的布局,往往在换头处花招百出,或者似承似转,或者陡然怒转,于空际大转身,忽生顿挫空灵之妙。 但文无定法,也有打破上下分片的,两片一气贯注,完全浑融一体。如上面提到的六弃疾的壮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前面一路狂奔,气壮如雷,到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才陡转,虽说形式上分有两片,但文义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段。辛弃疾以纵横的才气豪情冲破了常规的分片形式,读者也不必以常规来规范他。

顺逆、错综 起结与过片是词的关键组成部位。如果从词的结构意义来考虑,就有了“顺逆”与“错综”之分。以时空顺序、逻辑关系等来布局谋篇,叫做顺,反之为逆。多重时空交错的结构,叫“错综”。 1、顺 a、先昔后今: 人的生命本体以时间的方式存在,文学是一种关于时间的艺术,从时间的流程来看,当然是从昨天到今天,从过去到现在,写作往往就随着时间的步伐勇往直前,写成了顺流而下的“流水状”。如上文所举李煜的《破阵子》和陈与义的《临江仙》,都是从忆昔开始,到如今完全不同于昔日的生活。此类词作,往往是说今非昔比,过去总是美好的,现在总是哀伤的,无限的伤感和怅惘在对比中不言自明。

b、从内到外: 从空间的位移来看,一般的顺序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次分明。比如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先写室内菊愁兰泣,再写罗幕外燕子双飞,明月穿户,下片转到独上高楼望远,从内到外,层层写来,脉络清晰。空间场景在转换,境界越来越扩大,从而丰富了词的内容。 c、由景及情: 这种写法在宋词里最常见,是很省事的套路。如上文所举的例子中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上片纯写落寞秋景,下片抒发怀乡之情。秦观的《满庭芳》(山抺微云),上片写景为主,景中含情,微云抺山,斜阳归鸦,下片以换头“消魂”二字直起抒情,以下情感的抒发便一发不可收,滔滔汩汩,无限伤离之情溢满纸外。

d、前因后果: 从逻辑的关系来看,正常的顺序是由因至果、由分到总、由特殊到一般。比如李煜的《清平乐》(别来春半),一起笔就告诉别人,这首词就是写离别相思的,因此,就下来就展开对别情的细腻描述。因为别,所以苦。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

2、逆 a、先今后昔: 这类抚今追昔的词,比较常见,往往用“因念”“犹记”等 有明显标志的词语,表示时间由今日转换到过去。如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上片写梦回酒醒后的落寞感伤,不由得想起去年春恨,下片“记得”二字领起过去与歌女小蘋欢聚的情景,表达了对旧情执著难忘的深情,过去与现在的苦乐对比也表明了世事的沧桑变化,令人怅惘不已。伤近,是文学 的一大母题,多愁善感的宋词尤其喜欢“向后看”。 b、从外到内: 如晏殊的《踏莎行》(小径红稀),上片写外景,郊外小径残红稀疏,原野上芳草萋萋,空中飞絮濛濛,树阴中隐隐现出楼台。下片写内景,辽落中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袅袅,时光在静谧中悄悄流逝,愁梦酒醒,斜阳满院。由外而内,词序井然。

c、由情及景: 这种方式也很普遍,词人用得很娴熟。比如张先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上片写午睡醒来后的愁情,下片纯写月下静谧的境界。 d、前果后因: 先说结果如何,再步步追寻原因,倒戟而入,逆流而上,新颖别致。如周邦彥的名作《夜游宫》:“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古屋寒窗底,听几片、井桐飞坠。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一路上写水面暮景、立看灯市、古屋叶飞、无眠夜起,按时序闲闲写来,不知词人到底有何心事?到最后三句才抖出谜底:“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原来都是一封情书惹的祸。再回过头看前面,就觉得那些话有了着落、有了深意,通篇便染上了情的光彩,更觉细腻委婉,没有一句废话,前面的结果描写用的是“层层加倍写法”。试想,如果把原因先说了,再说如何如何的烦恼,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力了。词人只是巧妙地换了一下顺序,词的魅力就增加了几分。

3、错综 一般来说,小令短小,可供词人腾挪的舞台不大,因此词中的时空顺序、逻辑关系的变化比较简单。慢词长调的篇幅长,词人正好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们常常通过回忆、梦境、联想、幻觉等手法、造成时间、空间的多重交错,转换跳跃,收到顿挫变化、回环吞吐的艺术效果。 柳永善作慢词,但他的章法结构一般是顺流而下,从头到尾,娓娓道来,是一种单方向的直线型结构。李清照的长调也基本如此,有时也多一两个波折迂回,比如《永遇乐》(落日熔金)由现在的元宵节,情不自禁地回想过去在中州的元宵佳节,最后又闪回到如今憔悴的元宵节,是比较常见的今-昔-今的三段式结构,有两次跳跃,但还是比较简单。时空跳跃交错、复杂变化,莫过于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如周邦彦的代表作《瑞龙吟》(章台路),词分三叠,由第一叠的现在,第二叠转到过去,第三叠抚今追昔,先说今,再犹记过去,然后回到现在的探春。多次从容地辗转于过去、现在之间,时空交错,极尽顿挫变化。《兰陵王》(柳阴直)的时空跳跃更急促更频繁,今昔反复回环,层层渲染,如同游走在中国古典园林,备极吞吐曲折之妙。吴文英的长篇巨作《莺啼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为写词煞费周章,多方出击,词作的章法结构多是多条小径交叉的环线型、立体型的结构。

雏鸟不慎掉落,父母拯救的瞬间 空中荡漾 词的布局谋篇关系到词的整体效果,结构的技法自然重要,前人对此多有精妙的体悟与总结。其中,被认为最妙的是,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却偏不入,而于其间传神写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什么是空中荡漾?看过空中飞人杂技表演的都知道,一个飞人在半空中飞来飞去,你以为他向左飞,谁知他只是一个假动作,马上借力飞向右了,惹来观众一阵阵尖叫声。刘熙载所谓空中荡漾的意思是说,上句提出了一个问题,下句本应该顺着回应,但词人偏不,而是故意扯开说别的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词就有了一波三折、波澜起伏的味道,就像在空中荡漾。

比如姜夔的《踏莎行》(燕燕轻盈)下阙:“别后书辞,别时针钱,离魂暗逐郎行远。”本来以下要接离魂追逐情郎远行后的情景,白石却刻画了一个幽蓝冷清的缥缈境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写伊人的离魂月下归去的孤清情景,从离魂远行到月下归去,一来一去,显得空灵荡漾。 又如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上阕前两句,欲说归期,愁容满面。后两句,却由此生发了一个议论:“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按常理,说到“有情痴”,应该就此借风月什么的进一步渲染一下离情别绪,但词人偏不接上意,而是反说“不关风与月”,不落俗套。下阕前两句正面写离别之难,可后两句却说“容易别”,看起来前后矛盾,但正因为这样欲擒故纵,来回折腾,才使得结尾两句“直须看尽落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形象饱满,栩栩欲动。整首词的情感表现得波澜起伏,顿挫有力,深得空中荡漾之妙。

“空中荡漾”,确实是词家妙诀,听起来有些玄妙。换句实在话来说,即“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比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斯为入妙。刘熙载的这句话说得更具体更具操作性。

展开阅读全文